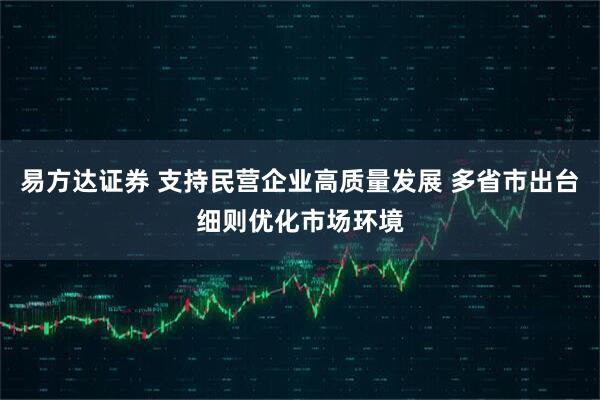九派新闻记者 冯翊吕德文每天要去武汉大学附近的广八路去打“卡”,晃晃悠悠地,来到广埠屯地铁站,围观一个象棋摊。摊前的人,往往用眼神打个招呼,然后安静地看着象棋摊,时不时点评一下棋局。围观的人中金多多,有退休老教授,还有骑手、小贩,还有一些路过的学生、白领,“不同群体的人都有”。他把它定义为“街角生活”,非常享受。作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,吕德文长期关注基层社会,街角社会自是其中应有之义,他常以“他者”的身份“躬身入局”,这一习惯很早就已养成,早在十多年前,他在华中科技大学任教时,就用这种工作方法,体验了一把“鲁磨路”。这是一条武汉洪山区的长路,约2.5公里,号称“武汉八大夜市”之一,那里聚集着很多小贩,也有很多城管,熙熙攘攘,十分热闹。吕德文深入其中,去那里摆过摊,也跟着城管巡查过小贩,获取了很多一手而又独特的“田野”资料。十多年后,他将这些资料、体验和洞察,写成了一本书《鲁磨路:城管、小贩与街头秩序》,向人们展示了鲁磨路上独特的“生活系统”与“街头秩序”,书中呈现了城管的治理逻辑、小贩的生存智慧以及各种不言而喻的关系和博弈。他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人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的城市——一个生机勃勃、充满包容和韧性的生活空间。

以下是九派新闻与吕德文的对话,音频版本请移步:https://www.xiaoyuzhoufm.com/episode/69085eff48dbe0eb562b756e?s=eyJ1IjogIjY3NTAxZjdmZWRjZTY3MTA0YWYzMzJmYyJ9【1】小贩的生存智慧九派新闻:为什么会选择鲁磨路作为一个田野调查对象?吕德文:鲁磨路在武汉是有一定知名度的,是文化地标,比如VOX,曾一度驻扎鲁磨路,因为它,武汉成了民间所谓“朋克之都”。它还是武汉民间号称的八大夜市之一,有武汉的江湖味、市井味。我之前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博士,毕业后留在华科工作了很多年,它作为我多年生活过的一个“附近”,我对它很熟。另外,2011年之后鲁磨路是一个重点整治区域。作为一个关注基层社会,喜欢从微观透视宏大社会进程的学者,鲁磨路对我有天然吸引力。九派新闻:书里有一个小贩让我印象很深,就是疯子爹爹李成柏,他对顾客说话很幽默,非常讨人喜欢,和鸡排哥很像。吕德文:有个纪录片叫《城市梦》,主角就是疯子爹爹,你可以看到,李成柏天然有镜头感,你以为他是演的,其实不是。他平常就是这样,个性特征特别鲜明,很适合公众生活,人越多,他的状态越好、越兴奋,他是个“街头表演家”。城管对他执法,他本能反应不是害怕,而是兴奋。他的情绪会上来,会调动一切智慧解决问题。李成柏来武汉不久,就受到了当地社区照顾,后来还专门给他一个亭棚,慢慢地他又把儿子儿媳妇接过来,他们接着生了小孩,在这里一直成长。他的生存智慧,是很值得敬佩的,有中国农民的韧性,这是特别好的一面。他的性格特征非常凑巧地迎合了国家市政管理的一个理念:疏、堵结合。疏在前,堵在后——城管执法首先是“服务”,然后是“管理”,最后才是强制措施,体现城市管理的包容性理念,鲁磨路的很多小贩,甚至大部分小贩,都受益于此。

转型前的鲁磨路。纪录片《城市梦》剧照。九派新闻:在街头金多多,普通小贩要处理同行与城管之间的关系,他们的生存智慧是什么?吕德文:先要占一个比较好的摆摊位置,“先到先得”,然后与同行进行差异化竞争,善用经营策略,像鸡排哥这样的小贩,在任何一个小贩聚集的地方,都有类似的小贩和明星产品。还有就是得放低身段,做一个真正的小贩。态度要温和,这是千百次经过顾客挑挑拣拣锻炼出的素养。哪怕像李成柏,面对城管很有气势,但顾客来了,立马满脸春风,更重要的是占据一个稳定的位置,不断积累声誉,不断建立稳定的顾客关系。最后,跟街角的头面人物搞好关系,至少沟通上做到无障碍。九派新闻:小贩有独立的生存底层逻辑,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。您说小贩它是复杂的,难以用文书档案进行标准化,如何理解这句话?吕德文:小贩内部构成,确实超乎我的想象。有很明显的分化,还有支配结构。同样是小贩身份,有些是老板,有些就是打工人。从调研结果来看,很多小贩和城管起冲突的事件中,小贩并不弱势,而是比较强势的,他强势所以才敢跟城管做斗争。大部分人,城管一来,就跑了。概括起来,就有两种群体:一种已经在街头占有了商业利益,它钉在这里,一种就是打游击的群体。比如很多大学生,很多外地人,还有一群自己种菜的老爷爷老奶奶。还有一些残疾人,要在街头摆摊讨生活。像鸡排哥这样的小贩,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自雇经营者。他不用雇佣别人,一个人就够了。大部分小贩是正经生意人,靠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吃饭,服从管理,会钻一定空子,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

吕德文调研期间,和学生在鲁磨路摆摊。图/受访者提供【2】城管与小贩的“博弈”九派新闻:你在书里边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,城管其实是小贩利益的保护者,这句话怎么去理解?吕德文:第一,对真正弱势的小贩,城管有一整套的制度和做法去帮助。我在鲁磨路城管中队调研的时候,大厅里面,就贴着小贩送的感谢信。街角确实是部分群体的避难所。这个功能的发挥就依赖于城管。所以,鲁磨路上有一些爱心摊位,书里提到的余斯淼,当年他带妻子来武汉治病,花了很多钱,没办法,来鲁磨路上卖板栗,武汉本地媒体也报道了,城管也知道,主动给他安置了一个爱心摊位,慢慢卖。李成柏就是多次受到城管和社区、街道的帮助,才能在武汉扎根。这种例子数不胜数。我还经常遇到很多乡下来的小贩,就持了一个村委会证明,或者残疾人证明,这些证明某种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合法性。但城管看到了,还是同情他,允许他摆。在街头,我看到了很多基层社会的感动画面。我认识的城管,他们每个人都帮助过小贩,发自内心地帮他找摊子,找位置,这其实是一个常态。第二,城管的工作方法给正规经营、想要通过摆摊来获利的人,提供了机会空间。比如时间差,城管自然而然在中午、晚上就要放开。放开不单单是因为上班的时间错位,更重要的是,城管部门自己就认为要给摊子一部分生存空间。这个群体还比较庞大,鲁磨路白天、晚上摊子加起来有一百多个,单夜市就有四五十个。城管作为执法部门,客观上承担了服务民生的功能,甚至很多社区安置一些困难群体,往往也会找到城管。这是城管制度内部运转的一个常态。第三,城管通过执法和管理,限制了那些想长期地占有街头利益的一部分食利者群体,把这些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群体约束住,普通小贩才有摆摊空间。它保护大部分的小贩利益。城管作为街头秩序的维护者,给小摊小贩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营秩序,可预期的利益空间。第四,城管能避免小贩之间非法的、不正规的恶性竞争。假设没有城管,“先到先得”的原则不一定能够被大家认可,不一定能贯彻下去,有可能是拳头硬的人说了算。【3】充满包容的街头秩序九派新闻:书的副题:城管、小贩与街头秩序。这个秩序应该就介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地带,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性的场域,有黑的有白的,但更多可能是灰色的。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,也是非常有韧性的秩序。吕德文:对的。这本书的最后落脚点就在于,城市共同生活如何可能。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,有个困惑,很多西方或者第三世界的城市,就是因为暴力冲突骚乱导致溃败。它们背后都指向一个问题:城市还能让大家共同生活吗?但我们国家的城市与之不同,它很有韧性,韧性的背后就是灰色秩序,过去很多人会觉得,国家权力扩张,必然会与个体权利产生冲突。我深入进去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比如城管和小贩之间,常态是默契互动,大家共同存在,虽然不是一伙的。他们都生活在街头秩序之中,那些路过的人也在接受这个秩序。大家认可小贩,因为自己也有需求,需要有夜市的生活,但是小贩也要被规制,不能把整条路给摆摊,那会影响出行。所以城市里很多关键的利益群体,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街景。这是中国街角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点。九派新闻: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性的结构。吕德文:对,我给你讲个事。我现在喜欢逛广八路,它跟鲁磨路很像,每天固定要去打卡,在广八路广埠屯地铁口,有一家百货店主老张在其门口街边摆了象棋摊,每天都有人在那下象棋。围观象棋摊的很多人,有一个很斯文的人,大家都叫他教授。有一个下棋水平最高的人,是个外卖骑手,没接单的时候要下两单。还有个高手,每天在这里边下棋,边等他妻子下班。这个象棋摊最能体现中国城市的包容性,它横跨各个群体,没有谁看不起谁,大家相遇在街头的象棋摊,建立了长期“共同”的街头生活。它是城市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,体现了街角生活的魅力。这种生活的特点是,随意进出,没门槛,路经此地的人可以吃小吃,见到熟人打声招呼,交往、行走,甚至阅读,它是特别有意思的街角社会。但内部又有规则,比如观棋不语、落子无悔,输了换人。在这种包容性的街头,不同生活方式的人,不同阶层的人,不同职业的人,汇聚在这里,呈现出特别有意思的街头生活系统。
【来源:九派新闻】
声明: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金多多,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,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。邮箱地址:jpbl@jp.jiupainews.com
富腾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